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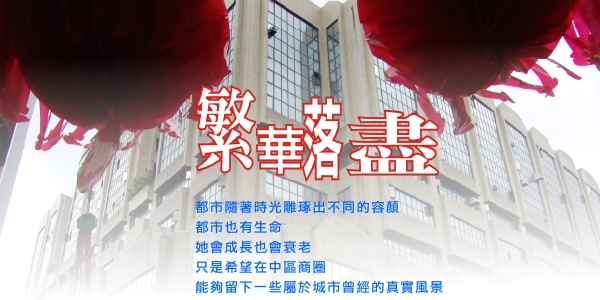
──中區商圈的沒落是必然的。
曾服務於臺中市中正路上的臺灣銀行健行分行研究員王明榮先生,為中區商圈下的最後結論。
一如人生的過程──生、老、病、死。我在繁華落盡之後的臺中市中區商圈,窺視城市的風景,在這曾是臺中市第一大商圈的市集中,親炙商圈的悲歡歲月,探索城市的靈魂。
二○○三年五月十八日,鋒面來襲,風雨飄搖,當天是自由路上《一加一影城》最後的營業日。《一加一影城》的前身是《東海戲院》,一九五九年《東海戲院》開幕時,當年一張票價十五元。
一九六三年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李存祿先生出版的學術專刊《臺中市發展的地理基礎》,提及臺中市市民的娛樂大致輪廓:「臺中市住民通常的娛樂是電影,本市電影院及戲院共十六家,其中以東海戲院設備最佳。」六○至八○年代,是《東海戲院》黃金時代,當時戲院營運狀況極佳,電影幾乎場場客滿,場外常常出現黃牛票的交易。電影院共一千四百個座位,賣座的影片可以連映一、二個月,那是個電影院風光的年代。站在時代轉彎的地方,「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林老闆有感而發。中區商圈的沒落嚴重打擊《一加一影城》的營運;加上開放外商在臺設立電影院,挾其資本雄厚及先進的經營設備,外商公司大舉攻下臺灣近七成的消費市場,本土老電影院更加難以抗衡。林老闆印象中《一加一影城》最賣座的影片,是一九九六年的《鐵達尼號》,距今已過七、八年;赤字經營電影院的心情無比複雜,每日營業成本逾一萬多元,而收入卻遠不及此。當對街的台中遠東百貨經營失利時,早於二○○○年結束營業;以家族企業方式經營的東海戲院,其壓力是常人無法想像的。
──現在來戲院看電影的有二種人:一種是失業的人、一種是沒有工作的人。
林老闆感歎現今冷清的二輪戲院成為失意落難人的避風港,而非娛樂場所。本土電影院淪為失業者暫時依存的失樂園,時代呈現兩種對比的差距,或許,這也是一場戲吧!每當在沉寂的夜裡,重回現場,在闐黑的環境,望著櫛比鱗次卻沒有霓虹閃爍的大樓,回想起曾在此觀看老電影的種種歡愉時光,經常不自覺地掉下淚來,找不到共同的記憶,被遺落的城市是何等淒涼,幕,落了。
商機一點一滴地消失,中區商圈的光環快速褪色,城市的方向歸零,街道隱藏著動人的故事。儘管生存的空間受到莫大的挑戰,還是有一群人執著地站在土地上。第二市場是中區商圈裡的傳統老市場,認識一些在地的前輩,他們帶著強韌的生命力與生存相互拔河。
昏暗的燈光下,阿枝婆婆總是一個人安安靜靜地顧守著生意,時間早已過了早市時間,附近的商家也都已結束休息。黃昏五點,阿枝婆婆依然守著不顯眼的攤位,努力地工作著,雖然生意清淡,攤位上仍有許多尚未賣出的蔬果,阿枝婆婆很有耐性地期待顧客。阿枝婆婆是第二市場裡傳奇的人物,傳聞她家境富裕,現今在第二市場擺攤只是一種習性的使然,一種自幼即已培養出的勤勞習性,總要有點工作忙碌才覺得算是生活。阿枝婆婆曾經遭遇一場大車禍,手腳有點殘疾,或許是生活中磨練出不服輸的個性,痊癒後的阿婆儘管身手不如往昔敏捷,晨昏依舊守著不起眼的攤位,譜寫生命的旋律。每次在第二市場看見兀自一人微笑的老阿嬤,心底總覺得生命真美,一種踏實的生命美感。
第一次和玉蘭阿嬤聊天時,第二市場外面正下著滂沱的午后西北雨,阿嬤的小孫子就躺在鄰近的攤位睡憩,大孫女則認真地站著寫作業。玉蘭阿嬤來自異地,年輕時即失去丈夫,為了生活,輾轉來到第二市場開始後半輩子的生活履歷。早期中區商圈繁華時,第二市場攤位一位難求,義豐線行的黃頭家嬤因為早年喪夫,基於同理心,應允玉蘭阿嬤免費在其線行騎樓下設攤販賣水果,並且在經濟不寬裕時伸出援手,使玉蘭阿嬤得以在生存的細縫中找到生命的基點。經過數年奮鬥,好不容易終於有了自己的攤位,原本販賣水果也改為經營服飾皮鞋生意,然而憑藉一名婦道人家,難免屢遭附近同行業商家的排擠欺侮。玉蘭阿嬤是個樂觀的人,四十年下來,早已體會出個人不卑不亢的生存之道,中區商圈的沒落,致使生意的經營倍受壓力,然而在玉蘭阿嬤的身上仍散發一種純樸又堅韌的氣息,不輕易向命運低頭。而今,子女皆已成家,也晉身為二個孫子的阿嬤,談起在第二市場落腳生涯的種種,依然清晰,真摯動人。
昔時的人文逐漸凋零,中區商圈沒落之後,不少商家眼見商機消失,紛紛放棄此地,轉移其他商圈發展;然而,總有些老字號的商家執著挺立於中正路上,不願輕易放棄。「義豐線行」黃老闆是第二代接班人,大學時代主修企管,對於人生的路,他有很大的感歎。創辦線行的老頭家嬤來自彰化和美,當時和美是臺灣紡織的重地,於是老頭家嬤遂經營和紡織相關的行業──線行。在早期臺灣傳統工業興盛時,中部紡織及製鞋工廠林立,義豐線行的生意商機由此展開,黃老闆至今仍會緬懷求學時代回家幫忙照顧生意的情景。那是一個有努力就有收穫的年代,黃老闆肯定走過的歲月路途。近十年來,中部的紡織及製鞋工廠早已轉移至大陸市場,加上中區商圈的衰敗,五十餘年老字號的義豐線行顯得不及過往輝煌,而老頭家嬤也往生八、九年了,經營線行的經濟壓力沉重,但黃老闆依然堅持守著母親傳下的家產,奮力生存,甚至栽培大女兒就讀南部某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以便傳承家業。對於未來,黃老闆不願多言,甚至坦言,線行的生存的空間已經愈來愈侷促。看盡繁華,生命巨大的起落,尤其是老頭家嬤辭世之後,頓感失去依恃的明燈;然而,不管生命如何黯然,總是得樂觀面對,老闆說他特別喜歡蔡秋鳳的歌,滑落於生命的輝煌,慢慢吟唱一曲屬於生命淺淡的情詩。今年初春,黃老闆步履老頭家嬤之路,罹患癌症告別人間,徒留未成調的人生之歌。
凋萎的第二市場,漸漸成為聚賭的地點,充斥地下經濟的交易。無力解釋其中的是非曲折,心底難免隱約疼痛,祈盼第二市場能找回屬於以往的繁榮;至少,裡面能呈現一些光明面。只要第二市場恢復生機,大量的人潮如同往昔進進出出,這些聚賭的行為便會無所遁形自然消失。然而衡視目前第二市場蕭條冷清的情景,成為地下經濟的溫床並不令人意外。
商業,是中區商圈的唯一賴以生存的命脈,一旦商業體系崩潰,中區商圈便等於宣告死亡。
六○至八○年代,是中區商圈的黃金歲月。由於地理位置位於市區中心,呈輻射狀,人潮匯集於此,成為交通的總樞紐,種種客觀環境的優勢,中區商圈成為中部最大的商圈。當時中區商圈的經濟腹地遍及中部五縣市,尤其每逢假日,商圈吸引許多外縣市的民眾來此消費,造就了中區商圈輝煌的歷史紀錄。
八○年代,泡沫經濟鼎盛時期,在現今中正路及自由路口聯福實業處,傳聞曾創下每坪五百萬的天價。只是榮景短暫,中區商圈由盛轉衰,就如同股匯市的持續崩盤,商家不是轉往其他商圈,就是結束營業,供需失衡的問題嚴重。在中區商圈,關閉商家的鐵門,四處都是張貼紅色出租的廣告。九○年代起,中區商圈內的百貨公司一家一家消失,二○○○年遠東百貨結束營業後,中區商圈的經營更為困窘,人氣的消失,讓中區商圈更形惡性循環,不見生機。一位旅居臺中的朋友如此形容中區商圈:
──中區商圈就如同一位已長大的孩子,卻仍穿著小時候不合身的衣服。
經過歲月的洗禮,經濟雖已凋敝,但中區商圈的人文風景如陳釀,有著城市深層歷史美學。
一九一七年,台中火車站興建,距今已八十餘年歲月。民國八十五年,這座火車站差點因改建計劃而遭折除,經過當地民眾及文化界的請命,火車站得以完整留存,並且已列入二級古績,成為歷史的建築。在這座充滿記憶與感情的火車站,是中部人共同的回憶景點。儘管物換星移,車站宏偉的氣勢至今依然教人動容。文藝復興風格的外觀,細部裝飾則融入巴洛克繁複的華麗,紅色的磚牆、正中的鐘塔,曾是台中市明顯的地標,而今,隨著時代巨輪的蹍轉而過,火車站裡的鄉愁依舊,只是缺少大城市該有的繁榮景象。
中區商圈很特別,有一條美麗的河川蜿蜒流經──綠川。在日據時代,她曾是一條美麗的河,清晨婦女集中於此浣衣。曾幾何時,綠川的景緻風華變調,成為市區髒亂的一角。前些年,台中市政府重新規劃綠川景觀,於是在綠川原址有了不同的風情,數度徘徊綠川,三月時木棉火紅地綻放生命的微笑,五月時驚鴻一瞥川流上白鷺的影蹤,都市裡蘊藏著荒野文明的感動。
一九三八年,座落於中正路和自由路口的彰化銀行總行誕生,當時銀行機構總行大都設置在臺北市總督府附近,彰化銀行總行是唯一立足於臺中的金融機構,對中部的資金挹注有著很大的助益,臺灣光復後第一任董事長即是士紳林獻堂先生。中區商圈沒落後,原本設立中正路的金融機構也因商機的喪失而紛紛撤離中區商圈,彰銀總行在中區商圈顯得格外重要。
中央書店停業,對於愛書人是個不小的打擊。曾是中部地區最富盛名的書局,對臺中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臺灣文壇前輩作家楊逵即是當時中央書局的常客。書局結束後,接手進駐的是一家婚紗公司,婚紗公司將原本書局的外表建築裝潢上現代的造型,今日已無法窺見書局的原本風貌,如今該家婚紗又不敵大環境的衰敗,經營不到一年便宣告撤離,更留下令人難以釋懷的破敗結局。站在中央書店的騎樓下,回想年輕時代,為追求學問、知識,蹲在中央書局內看書的情景,不禁泛起陣陣的愁緒。
時代的轉變在中區商圈發生巨大的變化,巡禮中區商圈,發現其中有光榮、有屈辱,有些事物甚至永遠地消失了。都市隨著時光雕琢出不同的容顏,都市也有生命,她會成長也會衰老,只是,總希望在中區商圈能夠留下一些屬於城市曾經的真實風景。初夏的某休假日,開車經過中正路,車內收音機響起熟稔的旋律:
雨水和車聲擁擠在窗口
我在都市的邊緣停留
少年的往事在回憶中消失
勤勞的人啊無聊的人啊
還有陌生的我在街頭遊走
白色的牆柱玻璃的黑幕
藏著改變社會的人物
告訴我,世界不會變得太快
告訴我,明天不會變得更壞
告訴我,告訴我
這未來的未來,我等待
告訴我,都市不適合流浪
告訴我,這是我居住的地方
告訴我,告訴我,這未來的未來,我等待
是張大春的詞、李壽全的歌《未來的未來》,一時興起,我跟隨記憶中的音符,一起高聲合唱:
──告訴我,告訴我,這未來的未來,我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