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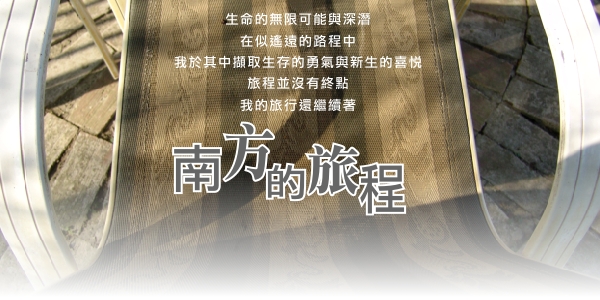
只是為了找尋生活的方向與意義,偕同朋友劉大哥一家人往久違的南臺灣出發,展開旅程。
在這塊生活了二十八年餘的土地,捫心自問,對這塊撫育我的土地,我是否真正凝神關注過。這受傷的土地繼續遭受無情的蹂躪,不知再經過多少的日子以後,這美麗島是否會成為文學家小說中的廢墟臺灣,當我還擁有生命的恩賜,該好好把握未來,從事些自認該完成的人生課題。有了這樣的信念,名與利都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掙開這層生存的壓力,我才得以真正在嚴肅的生命中展開旅行生涯。
朋友從海線的方向行駛,這一路的景緻對我言,皆是陌生的風景,車窗外的木麻黃與青綠的稻田,提醒我大地的豐饒。想起高中時在大甲求學的歲月,在青青草原寫生、攝影的記憶,也是同樣的風景。歲月賦予了不同的心境感受,由單純至複雜,這一段歷程不也是旅行的一種嗎?一種時間的旅行。
在旅行中難免會迷路,我把迷路當成是另一種旅行,在迷路的過程中,常會有意外的驚喜出現,我想那也是人生中美麗的邂逅。在嘉義,車往更陌生的方向行駛,竟意外錯過水上鄉,在嘉南平原上,我常會惦記朋友呂君的故事,在北迴歸線下,一個動人卻感傷的故事。同樣都有個愛酗酒的父親,同樣都有個堅強的母親,在蘭潭、仁義潭,與呂君彼此訴說不愉快的經驗。那時,暗地下決心要把朋友的故事寫成文學,六、七個年頭過去了,我的文學理念早隨臺北的歸鄉而埋葬,再也寫不出所謂的文學作品。
錯過了水上鄉,卻意外進入另一位朋友郭君的家鄉──東山鄉,多年不見,不知郭君在臺北土城的生活過得如何。往事如潮水漲退,一波波衝擊著,內心起起伏伏,我想起在軍中並肩吃足思想被禁錮的苦難,年輕得理不饒人的觀念早已不見,純真不見,正義不再,記起朋友在土城公寓以花盆栽植的九層塔,雖然長得並不盎然,卻也堅持對生命負責的態度,不肯輕易放棄對泥土的眷顧。祝福移植在臺北追尋幸福的朋友。
經過山路的曲曲折折,在玉井糖廠稍作休息。似乎台糖的每個糖廠都能教人回想起童年已泛黃的記憶,夕陽將至,生命喜悅的重擔沉沉壓在心底。
往甲仙鍚安山的路途中,天空染上一層層的陰霾,我暗自擔憂今天大概無法拍照,雖然眼前的風景越來越靈秀,當身置真正的空山靈語中,所有在城市遭受的挫折在此得以遺忘。登高望遠,在山與谷之間,我的心飄向遠方,我無法體會護守山園人員努力向我說的基督教義,雖是如此,我終是完整聆聽完一遍,法國的先哲伏爾泰的話:「我不同意你的話,但我誓死保衛你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山間終於灑下滂沱大雨,夜晚即將來臨,山巒在黯淡中逐漸沉默,離開錫安山時,四週一片寧謐,車子繼續在彎曲的河階地奔馳。我疲憊的闔上眼關閉起靈魂,在車內安詳沉睡,直到回到甲仙,意識才緩緩恢復。決定晚上寄宿妙通寺裡,寺裡有位大嫂紅塵時的故友,在歷經不愉快的婚姻後,削髮為尼,寺廟就在南橫的路途中,朋友劉大哥與大嫂互相對話,車內兩個小朋友安靜坐著,公路上偶而有車錯身,在這假日中,能拋開一切的雜務至大自然中徜徉,對我而言,是件幸福的事。一直幻想成為現代陶淵明,卻無法卸下五斗米的壓力,習慣在城市卑微的生活,對於尊嚴,早就不大理會,只是在人群中以最和平的方式生存,只有在夜晚來臨才偷偷溫習昔時的理想,把文學和藝術當成是心中最後一盞明燈,支持繼續生存的最後一道理由。
到達妙通寺,夜已深沉,抬頭仰望滿空的星子,思緒又回到軍旅時代。我太沉溺於從前,在屏東戍守的歲月,給予我甜美卻苦痛的烙印。我從不後悔走過的每一步腳步,在錯誤中我至少體會到智慧的清明,我想我大概知道未來生命的方向。在旅行和流浪之間,我會一筆一畫創作自己的作品,以嚴肅的態度。
經過一天的旅程,身軀的疲累是避免不了的,寄宿在清靜的寺廟中,雖然腦中的思路不肯安眠,倒不覺煩亂,在眾神的庇護中渡過安詳的一夜。
清晨四點,天地還是一片黑黝,寺中已開始上早課,膜拜完眾神,開始唱誦經文,在廣闊的神殿下,嚴肅的氣氛教人產生微醺的感覺。我不懂佛經的內容,只在經文中略為領受到慈悲的心境,尤其在波羅密多心經中,那恩典在心底徘徊,我暗自為今年初春早逝的謝大哥及在人世間仍得受苦的謝大線及足歲二歲的小朋友祈福。在謝大哥有生之年,曾為追求繪畫藝術下過一番苦功,雖然謝大哥從未正式受過學院的訓練,但在遺留的石膏像素描作品中,卻可看出謝大哥的才華與認真,雖未與謝大哥深交,得知謝大哥往生的訊息後,情不自禁在斗室中為謝大哥守靈、寫祭文,在「淚灑天堂」的輓歌中,盡情讓眼淚渲洩。渡過那一晚,我彷彿體悟些生命的脆弱與無常,我想說的是,天天重覆著浪費時光的缺點,盲目在生存中乞求肉體的溫飽,卻遺失了年少立定的理想,是件十分可惜的事。我起想起鍾理和、王禎和、洪醒夫等前輩作家,我想起梵谷、陶淵明等歷史人物,我的慚愧無地自容。為了什麼理由我把理想給放棄了,說來可笑,只不過是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點小挫敗而已,可幸的是自己還堅持良心與道德,在現實社會中乞求生活。若不是謝大哥的突然辭世,恐怕現在的我仍在重覆沒有營養的生活,在迷糊中一天天等著死亡的降臨。現在我把每一個今天都視為生命的最後一天來看待,假設在生命臨終前,我還有多少的事還沒有完成,這次的旅行,主要就為了拜訪文學前輩鍾理和文學紀念館。我不能再以任何的藉口原諒自己多年立定的心願,否則,當生命無聲無息消失之後,連嘆息的機會都沒有。
吃完早齋,終於有機會攝影拍照。夏日清晨的陽光,把四週重重疊疊的玉山山脈烘染得綠意盎然,妙通寺在大山之中顯出特有的靈氣。經過考慮,向劉大哥辭行,一個人決定回轉南方美濃前行。因顧及現今已在南橫公路的深處,實在沒有必要再教大夥只因我一人的心願,回頭重覆昨日的路線。同時,我也難以解釋說明為何要前去膽仰鍾理和前輩的理由,尤其面對兩位年紀還小的小孩,我想他們還不能體會倒在血泊中的作家代表的意義,我不能因自私而浪費大家的時間,恰好寺外就有經美濃、旗山的公車,班次雖少,只要有心總會到達理和先生的故居。於是劉大哥一家人朝更遠的深山目標前進,我一個人展開人文方式的旅行。
大約只等了半個小時,搭上公車後心底落實不少,詢問司機該如何才能到達理和先生的故居,司機先生詳細解說老半天,並在到站時提醒我下車。公車在狹隘的山徑中彎曲前行,沿途的景色盡是山野的豪放,好山好水,這裡該是另一個世外桃源。
到了美濃,接受公車司機先生的建議,搭計程車轉往鍾理和文學紀念館。在約莫七、八公里的路程中,和司機朋友閒話,他謙虛自己不知道文學,只是對理和先生苦難的一生及堅持的毅力有著敬佩的心情。下車時,他主動將車價由二佰五十元降至二佰元,我和他推拖幾次,他都不依,並說我從外地而來理應是客人,就是算是主人招待客人吧,我的心很是過意不去,環顧紀念館地處偏遠,恐怕司機先生得空車回美濃車站。
我是以朝聖的心情來瞻仰理和先生的,當我站在理和先生曾經生活的土地時,心底自是一陣暖流激盪;朝元寺就在紀念館不遠處,理和先生火化後靈厝的地方。我在心底暗自吶喊:「鍾老師,晚輩來拜訪您了!」進入館內,牆上掛著昔時的各式照片及畫作,我驚訝已故作家洪醒夫也親臨過這片土地,在洪醒夫的像片前我佇足許久。不能遺忘,是經由醒夫先生的「田莊人」,才得以進入嚴肅文學的世界,多年來在心情低潮時,只要重新翻閱前輩們的作品,心境便會澄清開朗,不再計較、不再封閉。我想著理和先生的「阿遠」和醒夫先生的「半遂湖仔的黯然歲月」,一種時代重疊交替,曾在年少時為這世間的矯情不平暗自打抱不平,在這鄉土文學世界中,我得以真正檢視內心逐漸凋萎的真實豪情,不想再去計較身邊的是是非非,該堅持的理想我不會再放棄。我曾迷失在人間洪流中一段很長的時間,看不清前方,看不到未來,在自怨自艾中糟蹋青春,而今青春不再,回首以往一段荒唐的日子,心底有太多的失魄。站在前輩的史料前,我狠狠下定決心,不再重覆空白無心的歲月,就算這輩子無法如鍾老師留下感動的作品,至少也要潛心閱讀名著,不將此生白白放浪在世俗鑽營中,也許人生該有另一種尊嚴的生活方式。我可以不去理會世俗的羈束,只有我自己有權力決定,未來該以何種方式,完成生命的方程式。我的心越來越清明,越來越堅強。
民國四十九年理和先生辭世,距離我出生的年代(五十六年),相差七個年頭,等我真正咀嚼體會出理和先生的文學滋味,已是高中年代,時間的流逝愈加顯露理和先生的文學光芒。當年理和先生屢遭退稿的煎熬,今日看來,卻顯示出某些事物的荒謬,時代的不盡合理,及悲劇英雄的悽愴,在心海蘊成陳年的佳釀。
看到已故作家施明正為當代作家的速寫肖像,心裡又是一陣痛楚。明正先生的筆觸蒼勁豪邁,經書冊印刷後,畫作的力量削減不少,我望著原稿,尤如水火交會,一時分不清冷暖,只在心底默默讚嘆。
在艱困的環境中走完一生的理和先生,臨終前曾交待焚毀生前所有作品,那是對生命一種最深沉的絕望嗎?
完成生命中一件大事,有如釋重負的自在,我如朝謁般追隨前輩的腳步,明白這是件寂寞的工作,然而我立定目標,無怨無悔將在這條文學的路途摸索前進,就算沒有任何的回聲和成績。
告別理和先生,我鼓足勇氣向位開車前來紀念館參觀的先生提出搭便車的請求。這位先生是趁假期攜同妻兒回岳父家享受田園風光,且妻的娘家就在附近,原本熱心的朋友只預計順路送我一程至公車站牌,然而在沿路的聊天溝通中,竟不知覺中送我回美濃車站,我的心中有著無限的感激。在路途中,陌生熱心的朋友沿路特意介紹菸樓、美濃紙廠、中正湖、東門城樓等美濃風物,我的心跟夏季的太陽一般光亮,這溫暖的人情,教我肯定人間中的善良與純真,想起鄭清文先生的小說「檳榔城」,也許這裡就是一座美麗純樸的檳榔城。我們在路途中,感嘆理和先生艱難的一生,及美濃隱隱約約的美麗風光,只可惜沒看到菸田等已消失的傳統景致,雖然彼此並不熟悉,但卻有相同的心情,收穫是如此豐富,我一個人在異地,卻有家人的歸屬感,並不孤獨、並不寂寞。
生命的無限可能與深潛,在似遙遠的路程中,我於其中擷取生存的勇氣與新生的喜悅,旅程並沒有終點,我的旅行還繼續著,在人生之中。
